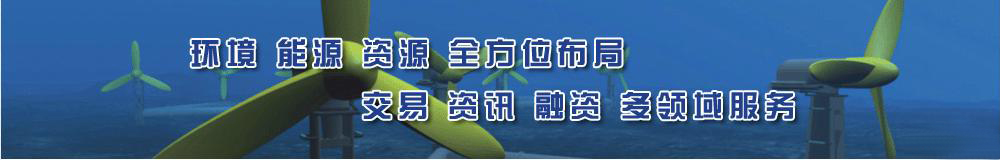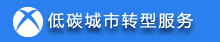在2月4日举办的中国碳排放交易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对中国开展全国碳排放交易的思路和时间表进行了详细论述,表示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并在2019年开始启动“高速运转模式”。全国市场初步将纳入6个行业年排放量在2.6万吨以上的企业,届时将有7-10个交易场所存在。
全国市场三阶段
蒋兆理说,全国碳市场的前期准备阶段为2014-2016年,随后2016年-2019年为全国市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希望能够全面启动全国市场运行,但具体要根据工作进展,比如可能在2016年夏季,或者秋季,目前正朝着2016年夏季启动的目标积极迈进。启动后,第一阶段将为三年,在此期间,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碳市场要素的工作,检验碳市场这个“机器”的运转情况,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大运行速度,会逐步加大力度。包括参与的行业、参与企业的进入门槛,也包括交易品种方面会有所控制,使得市场在初期保持适中的状态
在2019年后,也就是第二阶段,将启动碳市场“高速运转模式”,让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最核心的作用。包括准入门槛下降,企业数目几何级增加,配额分配进一步收紧等。
蒋兆理表示,碳市场建设有覆盖范围、配额总量、配额分配、MRV、注册登记、交易体系、履约机制、市场调控等八大要素,这八大要素是同等重要的,但是碳市场建设取决于水平最低而不是最高的那一块,因此要都建设好,这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未来保留7-10个交易所
蒋兆理说,回到碳市场本身,还有四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第一是法律法规基础问题,法律建设关系到碳市场的水平。七个试点地区用了不同层级的法律规定,尝试了不同的形式,有的是政府规章,有的是部门文件,有的是人大决定,而在法律制度的差异下,试点的运行表现、行为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全国碳市场来说法律层级就非常重要,要确保法律层次要足够高,法律约束力要足够强。
第二,企业参与。这在中国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有很多中央的企业集团,他们对地方子公司有超越地方属地化管理的权限,而后者是地方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是一个巨大障碍,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企业参与问题。
第三是碳排放数据准确性问题。碳交易和传统实物交易不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数据准确就非常重要。这不仅仅影响数据本身,而且影响企业参与积极性,和管制措施有效性。因此全国市场如何确保数据精确性,如何采用有效的核查报告方法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美国欧盟都有现成经验,而中国国情决定了还因按照国情加强工作。
蒋兆理说,去年国家已经出台了10个行业准则,目前在征求意见中,将转化成国家标准。同时对第三方管理也将有相应管理办法出台。发改委就将通过在线监测体系建设和监督执法队伍方面,全面推动,确保交易数据的准确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四,七个试点市场和未来全国市场是什么关系?是存在于全国市场之外的体系呢,还是全国市场就是把试点市场衔接起来?蒋兆理说,这些思路都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是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需要在确保流通的碳单位同质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现有7个碳市场的一些特殊规定。换言之,全国市场是设计一个全新的整体的市场,以此为基础兼容各地碳市场。
所谓兼容,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核算方法上7个试点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调整和统一。初步分析难度并不大,虽然看起来方法并不相同,实际上在制定过程中发改委进行了充分讨论,实际上方案是高度接近的,只需要微调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准入门槛的问题,全国统一碳市场一定是抓大放小,前期首批控制在“5+1行业”,年排放量2.6万吨规模以上的企业规模以上。对于已经存在的七个试点地区,要确保现有已经参加碳交易的企业无条件的纳入全国市场,用这种方式解决全国市场和试点之间的兼容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未来碳市场是有一个还是两个交易机构,还是每个省有一个交易所?经过反复讨论,发改委认为既不能只有一至两个交易机构的规模,又不能遍地开花出现更多的交易机构。理论上说,需要一定规模的交易机构为碳交易提供服务,因此中国需要7-10个交易机构之间比较合理。可以看到欧盟经验,涉及的企业数量并不多,碳排放量也不算太大,但保存了八个交易机构,各司其职运行有序。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碳市场,应该在7个以上,换言之,现已存在的7个试点地区的交易机构,今后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市场的交易机构之一。
同时,还有三个外部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法制建设,政策市场买需要法律,不仅是有法律,而且层级足够高;不仅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规定要更加严格,约束力要更加强烈,这是第一个外部条件。
第二个是良好的管理机制,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其中,中央有主管部门,地方有监管部门,只有衔接连续市场才能运转有效。中国和欧美国家情况不同,需要强有力的监管体系。
最后是资金支持,碳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措施,是一个公益性的市场,维护这个市场运行的资金一定不能是来自企业,或者运行参与方,必须是由地方或者中央财政的直接支持,舍此这个市场就不能有效建设,这是碳市场在试点阶段的重要经验,当运行市场的资金来自市场,就很难保证公开透明,影响碳市场运行,因此资金来源必须来自中央财政,来自纳税人的支持才能保证运行有序。
碳交易和碳税有先后之分
蒋兆理说在推动碳市场建设、企业参与的过程中,要保证高度公开透明,让参与方,利益方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只有这样才能透明地把市场建设好,是市场建设的一个基本考虑。
碳市场是一个由各种要素共同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要推动这一工程需要庞大的系统安排,中央,地方,企业的任务都进行了分解,只有责任到位,目标明确,权利清晰,才能保证按照安排完成建设。
蒋兆理表示,国家发改委对未来碳市场做了估计,在纳入范围方面,首先由五个传统制造业加服务业构成,传统行业包括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目前正在对这些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企业进行摸底,不久之后会列出企业清单。除此之外还想增加一个服务性行业:航空。航空业的基础好,也有很高的积极性,管理水平高,对贯彻落实中央节能减排工作政策有很好的基础。因此在未来2016年全国市场建设的时候,会考虑以这样的行业、企业作为首批的企业。
蒋兆理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碳市场排放量会涉及到30-40亿吨,如果仅仅考虑现货,估计交易额会在12-80亿元,如果进一步考虑考虑期货,交易金额会大幅增加,活跃性也将大幅提升,交易金额可能达到600亿到4000亿元,这些数据都是有测算基础的。
蒋兆理说,为了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碳市场工作,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好判断。第一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和全国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两者如果不协调好,难以发挥碳市场作用,但如果把直接把排放总量看作碳总量,企业将不堪重负,则欲速则不达。只有客观的把握这两者间的合理关系,恰当的设定上限,才能确保碳市场合理运行。
除此之外,碳税也是一个重要手段和重要选项,蒋兆理说,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碳市场更适合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碳税可以发挥补充作用,但时间顺序有先后之分,碳市场初步建成之日才能是碳税启动之时,这两个政策不能同时推进,既有经济学规定的考虑,也有政治上考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有清晰判断。
蒋兆理说,从建设时间来看,2014-2015年是碳市场建设最最关键的时期,要把所有的工作通过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检验标准,按照施工图推进,才能确保碳市场建设。对于各个要素,比如配额总量,覆盖范围,mrv,注册登记系统等,也都在做了具体分析。比如注册登记系统,在去年7月份已经投入运行,通过ccer检验了这套体系的完备性。对配额分配方法也进行了大量调研,模拟进行企业分配。MRV系统在进行各种测试,和认监委讨论如何授予第三方机构的资质,认定法律和相关规定等。“我想,通过这些努力,一定能够实现到2016年之后真正启动全国碳市场,”蒋兆理说。(水晶碳投分析师 张晴)
来源:水晶碳投